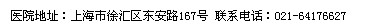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产后心肌病 > 心肌病饮食 > 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
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
大荒羁旅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
作者:朱晓军
引言
《山海经大荒北经》开篇则云:“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有人说,“大荒”指的是东北。后来,辽宁和吉林从“大荒”挣脱出来,只剩下“大荒”以北的黑龙江还荒着,于是黑龙江被称之为北大荒。再后来“北大荒”越来越小,被定位为“,横跨东经°40′到°40′的11个经度、纵跨北纬44°10′到50°20′的8个纬度之间,总面积5.43万平方公里。”泛指为黑龙江省的垦区。世界仅有三块黑土带,一块在美洲――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一块在欧洲--第聂伯河畔的乌克兰,另一块在亚洲――中国东北角。北大荒属于黑土地的一部分。
年,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将原东北农垦总局所属农场和部分省属农场合编成5个师,辖58个团(后扩大发展到6个师)。12月11日,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从此中国出现了“知青”,万有知识或没知识的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猎得“知识”,成为知青。其中的54万北京、上海、天津、杭州等城市的踏进衰草寒烟的北大荒,屯垦戍边,保家卫国。他们成为继十万转业官兵之后的又一创业群体。
十年后,轰轰烈烈的知青时代结束了,知青潮水似的退去了。北大荒变得寂静了,更为荒凉了,农机没人开了,学生没人教了,地没人种了。现实是冷漠的,欲望是无情的,知青的爱情和婚姻大抵返城绝望的产物,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之中的慰藉;当“柳暗花明又一村”时,往昔慰藉陡然变成负担和累赘,分手和离婚就不可避免了。在那些日子,“广阔天地”随处飘零着婚姻与爱情的碎片。先后有50万知青离开了北大荒,告别了黑土地,回到那没有伸出双臂拥抱他们的冷冰冰的城市。
可是,有两万多知青留了下来。留下,需要的不仅是智慧,还有勇气和魄力。这些知青像沙滩上的贝壳,眼巴巴地望着同车厢来的老乡和同学潮水似的从身边离去,他们望着空荡荡的操场,空荡荡的知青宿舍,空荡荡的炕铺,心也是空荡荡的,蓦然一声南归雁啼,惊落他们两行泪水……
下乡的理由都是相似的,留下的原因各不相同,或为爱情婚姻,或因工作和住房,或觉得在北大荒更能实现人生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留下来的知青大都是勇于担当家庭和社会责任的,他们放弃了“以我为先”的生存法则,放弃了朝思暮想的城市,放弃了和父母团圆的机会,放弃了再做城市人的梦想……
我是在年开始采访留守北大荒的知青的,14年来去过黑龙江畔、松花江畔、乌苏里江畔,到过红兴隆垦区、建三江垦区、宝泉岭垦区、牡丹江垦区的几十个农场,采访过一百多名知青。他们让我感受到另一种人生,让我激动和感慨,体味到质朴的高尚,体味到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承诺,什么叫人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过去40年了,对30年前返城的知青来说,苦难和风流已成为耐人寻味的怀旧,对留守北大荒的知青来说,知青的历史还在延续。这些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的人还拥有一个跟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称谓———青年(在北大荒知青被称为青年)。北大荒人称这些将步入老年的知青为“北京青年”、“上海青年”或“杭州青年”……在北大荒,他们永远是青年(知青)!他们是最后的“青年”、永远的知青。
一、女知青的婚姻———世俗无解的方程式
知青大返城时,嫁给当地人的女知青面临一场严峻的抉择:是离婚弃子返城,还是为爱人和孩子留下来?这不仅是对爱情和婚姻的考验,也是对这些女知青的责任、道德和良心的检验。
我在一本书中发现这样的文字:云南某农场有知青余人,在年10月以前,有人登记结婚,余人未婚同居。在年春夏知青大返城时,有多人办理了离婚手续,绝大多数未婚同居者分道扬镳……“如黎明农场3连,原有知青人,大返城时,已婚10人,未婚同居者人。单身者是一位心灵受过创伤,心态不健康的女知青。”由于这些已婚或未婚同居的知青“来自不同的城市,大返城时,结婚的10对全部离婚,未婚同居的说声再见就各奔前程……”
我没查到大返城时北大荒的离婚统计资料,也许根本就没有,当时许多部门都瘫痪了,学校缺了老师,医院缺了医生和护士,连地里的农机都没人开了,这么多重要的事情都没人做,还会有人统计返城知青的离婚率吗?我在采访中听说,当时离婚的知青特别多,其中有真离的,有假离的,有弄假成真的,也有弄真成假的。
有位知青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上海知青跟当地的妻子办了假离婚。他对妻子说,我回上海站稳脚跟就回来接你和孩子。妻子等了一年又一年,突然听说丈夫在上海早已找到工作,正在跟一个上海姑娘拍拖。妻子半信半疑地跑到上海,丈夫说,他下个月要跟那个姑娘结婚。妻子说,我们是假离婚!丈夫说,离婚证是真的。他请妻子原谅,他不可能再回北大荒了,也不能在上海打一辈子光棍,只好委屈她了。他说,这不是他的错,是社会的错。妻子流着眼泪离开了他的住所。第二天,黄浦江漂起一具女尸。那位北大荒女人投江了……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未婚知青心目中返城第一,爱情和婚姻第二。在“第一”希望渺茫,甚至绝望时,他们才会考虑在北大荒谈恋爱和成家。有时命运偏偏捉弄人,有的知青前脚登记结婚,返城的机会后脚就来,一些最渴望返城的女知青就这样留在了北大荒。
1“北京盲流”与“坐地炮”的爱情坚守首次入荒采访时,从哈尔滨到佳木斯,我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
那时,黑龙江国营农场管理局还在佳木斯站前边的小楼里。我穿过像地道似的走廊,在一间巴掌大的办公室找到了《农垦日报》副总编辑吴继善。他听说我要采访知青,建议我去饶河农场。我对饶河知之不多,仅知道那地方离珍宝岛不远。
第三天天刚亮,我就坐着长途客车出发了。车出城不远就告别柏油路,颠颠簸簸,摇摇晃晃地向前开着。司机说,几天前下过一场暴雨,佳木斯开往饶河的客车停运了,今天刚刚开通。
我在继善的办公室读过《饶河农场史志》,上边写道,饶河农场位于乌苏里江畔,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年,我军部队的名官兵在这里点燃烧荒之火。年3月19日,农场改编为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22团。~年间,北京、上海等地先后有11批知青来团,共计人,其中有北京知青人……
在这名知青中竟有4位跟当地户殷家的四兄妹结为连理,其中有三位是首批下乡的北京知青。潮起潮落,留下的知青已不足百人,跟殷家兄妹结婚的知青先后返城,北京知青李惠敏和孩子办回北京后,丈夫殷汝芳没办去,她只好辞掉工作回了农场;殷汝芳的一位妹夫办回北京后,妹妹办不去,他只好重返北大荒;殷汝芳的另两位妹妹一个随丈夫办到北京,一位随丈夫办到佳木斯。李惠敏人回了饶河农场,可是户口还在北京,当地人戏称他们夫妇为“北京盲流”的妻子、“坐地炮”的丈夫。
车到饶河农场时,昼夜已完成交割,远处漆黑一片,近处灯火寥落……
当晚,我找到吴继善介绍的那位场长。他看了看我的采访名单,无奈地说,你要采访的知青多数不在场部,秋忙很难给你派车。另外有的连队道路不好,雨后车根本就开不进去。我说,能不能借我一辆自行车,我自己骑车子去?他说,骑自行车下连队是绝对不可能的,两个紧挨着的连队相距也有十来公里,我们尽量安排吧。
还好,李惠敏的丈夫在连队当书记,得信后派了辆北京吉普把我接到她家。李惠敏热情地接待了我。她已变得像泼辣、爽快的东北女人,不过身上还保留着城市的痕迹。
对知青来说,有一个日子是绝对不会忘的,那就是下乡的日子。李惠敏是年8月30日下乡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下乡到了数千里外的“反修前哨”乌苏里江畔,怎么能不想家?李惠敏她们累了想家,苦了想家,不苦不累也想家。“男愁唱,女愁哭,老太太发愁乱嘟囔。”李惠敏想家就哭,好像泪水能把想家的念头冲走似的。女孩想家具有传播性,一个人哭其他人就跟着哭,凄惨的哭声不时从女知青宿舍钻出来,飘荡在夜色茫茫的荒原。
爱情是对付所有苦难的一贴膏药。下乡不久,情窦初开的李惠敏就和制砖排排长殷汝芳相爱了。殷汝芳是位性情耿直倔强,办事有板有眼的当地青年。当时兵团明令禁止知青谈恋爱,他们俩人被营里抓了典型,大会检讨,小会批评,小殷还被关了七天禁闭。
接着,一场大水把他们的连队冲垮了,殷汝芳被分到13连,李惠敏被分到16连,这对恋人被强行分开了。16连的条件特别艰苦,连电话都没有,临别殷汝芳偷偷送给李惠敏一盏小马灯,那盏马灯温暖了她一个个寒夜。白天,她跟连里的知青上山伐木,两个知青一把锯。天气冷得伸不出手脚,她把所有的毛巾都包在了脚上,把脚塞进42码的棉鞋里都不管用。冬天熬过去,总算把春夏盼来了,哪想到新开垦耕地的蚊子特别多,一只只像饿死鬼托生似的又凶又狠,叮住就不松口。用手拍一下脸,满掌都是蚊血,不!自己的血。李惠敏用毛巾把脑袋包得像粽子似的只露俩眼睛,结果还是躲不过蚊子的袭击。秋天就更苦了,割豆子腰累得像断了似的,她只好跪在地里割,半生不熟的馒头送到地头,咬口就能看到冰碴儿。
这种日子要没有爱情怎么挺得过来?
年春节,这对饱经磨难的恋人终于结为夫妻。李惠敏没有告诉对这门亲事坚决反对的父母。婚后,她休了下乡之后的第一次探亲假,回北京住了3个月。母亲要留她再多住几天。
“不行,连里不准超假。”她坚定不移地说。
母亲哪知道李惠敏已怀6个月身孕,再不走就露馅了。回到农场不到3个月,她就生下了儿子。
据《饶河农场志》载:“年知青大返城时,有0多知青离场,造成了生产人员严重不足,不少生产队拖拉机没人开……”
李惠敏看跟自己同一车皮来的战友像鲜活的鱼儿似的随着潮流走了,自己却像贝壳留了下来,急得团团转,最后得医院。殷汝芳望着病榻上的妻子,心里十分矛盾。结婚以来,每当听说某某知青为返城抛弃了爱人和孩子,就像石头落进心池,扰得他多日不得安宁。当时北大荒将知青喻为“飞鸽”,将当地人喻为“永久”。“飞鸽”和“永久”是享有盛名的两款自行车。这两种自行车一个是天津产的,一个是上海产的,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款式上差异都不大,可是用来比喻人那差别可就大了去了。“飞鸽”意味着暂栖枝头,将会远走高飞,“永久”却像黑土地上的老榆树,根深蒂固地扎在那里。
年,李敏惠的返城手续办下来了。11年来,做梦都盼返城这一天,户口准迁证拿在手里,那种渴望竟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亦难,去亦难,家和丈夫都带不走,她和孩子回去还有什么意思?罢,罢,罢,她一狠心把那生不逢时的准迁证撕了。这一纸准迁证来之不易啊,她母亲在京城求爷爷告奶奶地活动了多少年?她的父母还望眼欲穿地等她回去,殷汝芳把撕碎的准迁证粘上了。
李惠敏办回北京后,又返回饶河生下了女儿。户口在北京和在北大荒感觉就是不同,这回李惠敏走到天涯海角也是北京人了,她在北大荒住了下来,女儿两三岁了她也不张罗回去。她不急母亲急,怎么能这样过一辈子,这样返城还有什么意义?年,母亲来了,说父亲的单位要分房子,李惠敏和孩子回去就能多分几平米;还说李惠敏的关系是办回去了,可是工作还没有落实,怎么能猫在农场不回去?
李惠敏跟着母亲走了,她一步三回头,舍不得家,舍不得汝芳,泪水一滴滴地落在地上。母亲生气地说:“哭什么哭?像再也见不到面似的。”李惠敏一听不禁号啕大哭,她哭女儿也哭,站在一旁的殷汝芳也泪水潸潸。
年春节前,殷汝芳病倒了,躺在炕上思念着妻子和孩子,越想越苦,越想越绝望,三千里路云和月,想也见不着。
“大哥,医院去吧。”连里的哥们儿说。
“不去。”殷汝芳说,医院又解决不了他对妻儿的想念。
“把你送你妈那儿去吧。”
“不去。”
“把你送火葬场去吧。”哥们儿见这人不进油盐,气恼地说。
“行,你就把我送火葬场去!”
作为男人没给妻儿以幸福,反倒成了负担,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北大荒的冬季天黑得早,好似太阳攀到中天就轱辘到山下,将夜幕刷地拽了下来。归巢的鸟儿梦呓似的凄啼两声,是呼啸的西北风惊扰了好梦,还是寒冷横在那儿让它钻不进梦乡?李惠敏抱着女儿,牵着儿子,踏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家属区。回北京后,李惠敏谋得一份工作,同事听说她的丈夫是“坐地炮”,还留在北大荒,都劝她离婚。劝她离婚的何止同事,亲朋好友有几个希望她这样过下去?可是,她怎么可能离婚?她和殷汝芳不仅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恋,而且他还是两个孩子的爹。近家情更迫,汝芳的病情怎么样了?她知道他生活能力差,感到内疚,没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可是,她分身无术啊,再说母亲把他们娘儿仨办回北京容易吗?她刚有份工作,眼看就要转正了,哪能说请假就请假呢?春节前夕,她写信让他到北京过年,信刚投进邮筒就接到指导员的电报和元钱的盘缠。电报上几个黑字像一块块磐石砸在她的心上:“汝芳病重速归。”她拿着电报哭着跑去跟领导请假,回家收拾一下就领着孩子赶到火车站。
突然,眼前人影一晃,竟那么熟悉,“儿子,快喊你爸,快喊哪!喂,汝芳!”还没等儿子喊,她就喊了起来。那人影愣了一下,循声疾步过来。李惠敏急忙把怀里的女儿递过去,“女儿,快叫爸爸!”女儿打量一下他,怯生生地叫了一声:“舅舅。”殷汝芳抱过女儿,心一酸眼泪差点儿掉下来。
李惠敏一进家门就愣住了,这还是家吗?墙角挂满蛛网,地上一层烟头,炕上扔着脏袜子和罐头盒子;再端详汝芳,满脸憔悴,衣着邋遢,白衬衫已变成深灰色,抑制不住地哭了。第二天,她就抱着盆洗衣服,连洗三天。汝芳抚摸着洗得干净透亮的衬衫哽咽着说:“我好久没穿这么干净的衣服了。”她的眼泪流了下来,决定不回北京了,不管是苦是累,吃好吃孬,也要和殷汝芳在一起。
李惠敏的户口和工作关系没迁回来,在农场没有工作,只好在家养鸡养鸭,还养过海狸鼠。那些年农场不景气,她就卖鸡蛋鸭蛋供两个孩子读书。有人说,李惠敏,你也太傻了,丢了北京的工作,跑回来养鸡养鸭。也有人说,李惠敏,农场工资都不发了,你咋不回北京呢?
她说:“不发工资也不是我们一家,我咋也不能把你大哥扔这儿自己走啊。”
殷汝芳愧疚地说:“我这辈子谁都对得起,就是对不起李惠敏,欠她的实在是太多了。”
在采访时,李惠敏实在地说:“不管怎么样,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要说留在这儿一点儿不上火那是瞎话……”
7年秋天,又是秋天,我要去北大荒采访时,给吴继善打了电话,请他再帮助联系我过去采访过的知青。不巧,正赶上《农垦日报》创刊50周年,他忙得焦头烂额,可还是在百忙中帮我联系了几个农场。饶河农场说,殷汝芳退休了,跟李惠敏去北京了。我屈指一算,李惠敏已经55岁了,不返城的话也该退休了。从组织关系上说,她是返城知青;实事求是地说,她在北大荒生活了将近40年,还应该算是留守知青。
2天津知青黑龙江边赫哲人家的媳妇勤得利农场地处同江市境内,北依黑龙江,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南面是一望无际的三江平原。农场有两万多人口,汉族占91.1%,其余为满、壮、赫哲族等少数民族。第一次去建三江垦区采访时,听说勤得利有一赫哲人家的三个兄弟,老大和老二分别娶了连里两位漂亮的知青,一位是上海的,一位是天津的,老三跟北京知青谈一场恋爱没成,最后找了一位吉林的。
赫哲族人世代居住在黑龙江,是我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仅有人(其中包括那两位知青的儿女),他们远离城市,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边,靠捕鱼为生。大都市姑娘嫁过去,在心理文化上能相融吗?婚姻能否幸福和长久?
我一到勤得利农场就跟工会干事柱子打听这两位知青的情况。柱子说,她们在勤得利。
“这不就是勤得利吗?”我蒙了,难道我还没到勤得利?场部门口不是戳着“勤得利农场”的牌子么?
柱子解释说,勤得利是勤得利农场下边一个地方,那里有个发电厂。
勤得利距场部挺远,那几天刚下过雨,路特别不好走。去采访那天,柱子跟场部要了一辆北京吉普,这种草绿色的吉普车在城市已属“鹤立鸡群”,在北大荒这种“鹤”也不多见。吉普像醉汉似的摇摇晃晃地行走在翻浆路上,人在车里就像路边的水麦草忽左忽右,前仰后合。大约一个小时,吉普车晃进了一个镇子。
“那就是发电厂,现在倒闭了。”柱子指给我看。
我望了望那座寂然无声的工厂,门前冷落凄凉。它让勤得利在黑夜有过光明,让寂静的荒原有过机械轰鸣,此时却到了弥留之际,哀戚地望着陪伴自己度过数十年的黑龙江,望着北大荒的蓝天白云,望着当年车水马龙的街巷和从它身边走过的行人,等待着最后的时刻……
柱子说,发电厂亏损严重,维持不下去了。突然前边聚集着一群人,柱子急忙让车停下来,他跳了下去,将人群中最活跃的中年女性拽了过来,两个男的追着那女的问道:“你去不去了?”
“有记者来采访,我一会儿就回来。”她摆摆手,一转身上了吉普。
“她就是你要采访的那位嫁给赫哲族人的天津知青苏桂兰。”柱子介绍道。
我看了看她,眼睛不大挺精神。苏桂兰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她说她是发电厂的职工,几年前内退了,有些事还没得到解决,他们想去场部找领导理论理论。她说着一口东北话,只是个别字眼有着像果仁张似的津味儿。她说话爽快,有股敢说敢干的劲儿。
车绕了弯驶进家属区,那是一片旧砖房,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还算上等房。房子的格局有点儿像串联式电路,进门是一道狭窄细长的厨房,一通到底,拐弯进去是朝南的客厅,大约十二三平米。客厅北边有间七八平米的卧室。客厅里摆着一张单人床、一对简易沙发和一套样式跟房子同样过时的中高低柜。一片没织完的渔网拴在窗户上,织网的是位头发花白、有着赫哲族特有的宽阔脸庞、突出颧骨的男人。他站起来,用憨厚的微笑表示欢迎。苏桂兰说,他是她的丈夫付忠喜。
我想,她为这位赫哲族男人放弃了天津,他们的爱情肯定轰轰烈烈、刻骨铭心。苏桂兰却爽朗地笑着说:“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
真不可思议,没有爱情就跟当地人结了婚,放弃了返城?我想起《北大荒之歌》:“第一眼看到了你/爱的热流就涌进心底/站在莽原上呼喊/北大荒啊我爱你/爱你那广袤的沃野/爱你那豪放的风姿/啊……”难道她对他不是一见钟情?跟北大荒一见钟情也不见得非嫁给付忠喜呀,当年青年多着呢。再说,当年的北大荒该不会有那么大魅力吧,它又不是香格里拉。我采访过那么多知青,还没听说谁一眼就喜欢上这疙瘩,再也不想走了。
不出所料,苏桂兰第一眼看见勤得利时别提多失望了,她和姑娘们站在卡车上,眼泪汪汪地喊道:“这哪有绿色的营房?哪有草坪?哪有……”那种被欺骗的感觉在心里翻滚着,弥漫着,她最渴望的就是在卡车上不下来,让团里把她们送回车站,让她们回家。
当初,27团去天津领知青的人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手拿枪杆,一手拿锄头的部队,兵团战士是不戴领章和帽徽的军人,我们是按部队的编制,团、营、连、排、班,住的是一排排绿色的营房,吃的是白面大馒头,衣食住行和部队没有两样……”
苏桂兰的热血沸腾了,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一杆钢枪,一身戎装,对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多么具有吸引力?当然,最实惠的是那随便吃的大馒头……当时,城市居民的粮食是定量供应的,每人每月只有几斤面粉和大米,其余是粗粮,绝大多数人家饭都吃不饱,哪里吃得上白面大馒头?
苏桂兰家境贫寒,家里七口人靠父亲一人的56元工资生存,家里住房也很紧张,一家人挤在9平方米的小房里。白面大馒头和绿色军装,多么令她向往!她报了名,穿上土黄色军装,上了知青专列。火车没白没夜地跑了好几天,最后在铁道线的终点,一个叫“前进”的小站停下来。苏桂兰他们爬上卡车继续前进。天快黑时,他们不再前进了,到了目的地———位于黑龙江边的16连,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原野和几间破草房,她的心像旷野里的芦苇一样荒凉。
天像漏了似的不停地下雨,下得心都阴乎乎的。他们下雨也不休工,要到地里割大豆。割一天大豆,浑身就像散架了似的,回到宿舍两条腿都上不去炕。半夜时分,突然听到紧急集合令,他们以为苏修发动进攻了,惊惶失措地爬起来,张三找不到裤子的另一条腿,李四的上衣被王五穿上了,王五的只剩了一只……他们盔歪甲斜地赶到集合地点,连长下达命令:“山上发现苏修特务,紧急搜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他们胆战心惊地在山上忙活半天,搜到的特务竟是一头野猪。
不论生活是艰辛还是快乐,已被岁月带进记忆的沟壑。苏桂兰渐渐成熟了,脸上的稚气褪去,出落成了眉清目秀的大姑娘。
年,23岁的苏桂兰从天津探亲回来,几位老乡就跑过来问:“小常宝,你谈的对象家里同意啦?”
自从她演过《智取威虎山》中的小常宝后,战友们就叫她“小常宝”了。
“什么对象,我和谁对象呀?尽瞎扯。”她莫名其妙地说。
“你自己跟谁搞对象还不知道,装什么糊涂?”老乡笑了笑。
这一笑,把她笑得不安起来,越是不安越想弄清楚,越想弄清楚老乡就越不说。在那贫乏单调、缺少娱乐的日子,这种传闻比闪电还快,没几天的工夫就有六七个人问过她。她被搞得一头雾水,弄不清是哪个空穴来的风。
她从农工班调到炊事班后,炊事班就成小伙子北京现在治疗白癜风大概多少钱北京哪家医院能治白癜风